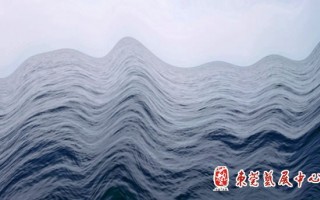强调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是戏曲随时代前行的既定方针。新时期以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借“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自信”之势,精品迭出,而现代戏却一直未见起色。于是,21世纪戏曲发展繁荣的重要指针似乎对准了现代戏的创作。在第9届中国艺术节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现代戏的创作成果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展示。这些剧目展现了戏曲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关注现实生活,弘扬主旋律”的时代使命,充分显示了戏曲对现实题材的艺术表现能力,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的把握能力,尤为难得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戏曲程式难以融入现代表达的瓶颈,出现了不少连接现代生活的新程式。
在对现代题材的关注上,北方的剧种向来更为积极、主动、热烈并充满激情,在内容选择上,立足于现实生活与主旋律的要求,所呈现的舞台风貌,无论是演员,还是整个创作群体,都有一种能感染人的、向上的力量。同时,这些北方剧种的剧目内容都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处理,有利于剧种对剧目的驾驭、演员对人物的表现,而这种“艺术简单化”的方式运用于颂扬先进和宣导政策也简洁而直接,能迅速引起普通观众的共鸣。或许正是剧种的内在需求与体制的外在动力,使得北方剧种的剧目在处理现代题材时,始终饱含鲜明的、突出的、不断强化的主旋律色彩。
如秦腔《大树西迁》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将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交大内迁西安支援西北建设的历史从尘封中开启,细密地展开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奉献”、关于“大爱”的篇章。在有着无数知识分子“南来北往”群体迁移事件的特殊年代,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历史纷繁复杂又常散落无迹,事件早已载入史册,对群体的命运多是无暇顾及的,而《大树西迁》让我们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有着崇高理想的一个群体,一代甚至几代人为国家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所处的无疑又是一个蓬勃向上而活力四射的伟大时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高亢激越的秦腔唱出的“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不仅是一种生命誓言,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
现代题材剧目以人为关注点
在特定的时代,戏剧创作迎合主旋律的需求,本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理想、信念、信仰、奉献、执著、大爱、大我”等精神语汇一旦脱离了个体生命的承载,即如无根浮萍,虚妄而浅薄。在现代京剧《飘逸的红纱巾》中,天真的、纯洁的、对革命抱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妙龄女子方斐,在烽火连天的岁月经历了战火和牢狱的生死考验,期间还有爱情与生命的救赎,这本是一个在极富戏剧性的年代中极有个性的生命旅程,然而,剧中,年轻的方斐始终是一副无邪无智的模样,即便是在历尽艰难重新回到部队遭到怀疑和指责时,仍旧没有表现出些许失落、委屈、疑虑到决绝的心理波折,由此情感的冲击力被无限弱化。
再者,在关注现实时,有些剧目常由于急切地再现和表达,陷入“失真”的困境,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塑造多是如此。此外,在表现农村生活的现代题材剧目中,创作者显露出低俗化和小品化的倾向,有些剧目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性格缺少深入的认知,往往过于强化某些为人所诟病的不良习性,导致对农村和农民形象整体把握的偏颇。如在豫剧《村官李天成》中,将农民“红眼病”的劣根性过分夸大了,甚至以此作为情节推展和人物塑造的助力,显然是不合适的。另者,或许是受到“东北风”电视剧和小品的影响,戏曲现代戏舞台上经常出现小品气十足的对白和场景,甚至也出现了贬损农民、嘲弄残疾的低俗趣味。戏曲从来不乏丑角的逗趣,但大多都被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赋予智慧的幽默滑稽,其行为和语言常发人深省。
现代题材的剧目需要历史的宏大叙事,也要有个人的命运周折;需要角色的预设交锋,也要有人物的情感冲突;需要背景的多重指涉,也要有时代的浓烈气息。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可视为处理现代题材的标志性作品:纯真质朴、活力饱满的剧种气质契合了世纪之交农村社会变革的现实所蕴含的蓬勃的冲动与希冀;剧作择取农村代表性的现实事件“打工与留守”,表现既有民间信念又有现实理想的“大时代背景下普通女性”的悲情与自强。其中,女性情思的涓涓细流,因为有了时代的支撑,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宣扬主旋律所必须的“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社会价值,凄美的现实题旨与唯美的舞台表现缠绕绵延,时代的气场、生活的细节与人物的情感被诗化、戏曲化,在和谐隽永优美的韵味中铸就了崇高的剧目品格。
别林斯基说过:“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成为某一时代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相对而言,在对现实的表现上,话剧似乎更能进行自如的表达。话剧《黑石岭的日子》融会了多种艺术手法来丰富其表现力,其中,极为冒险地在“语言”的艺术中设置了“无声”的角色。矿山里一个坚实、隐忍、善良、无私的男人刘老黑因矿难损伤了声带,却默默而坚强地活着。
世事沧桑,他常常竭力发声而不得,而正是在这无声的间隙,他的愤懑、痛苦、自责、满足、喜悦、宽慰,依然汹涌如潮,倾泻而出,一次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剧中不断强调的主体精神内涵是“生死相依”,但更深层次的情感应该是黑子所背负的“一个人的生和九条命的死”所生发出的生命的伟大意义——回报和奉献。该剧有外部事件的集中和延续,也有刘老黑内心的争斗和抉择,有历史叙述的支点,也找到了指涉现实的着力点,并顺势而为,极为巧妙地解读和颂扬了政府关注民生、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伟大举措。
形式探索要坚守戏曲主体意识
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发展的趋势是“分化融合”的,戏曲也是如此。但由于很多剧目从剧本开始,戏曲思维便已弱化,在二度创作中,也不甚注重戏曲的结构,失却了“戏”的完整性,成就了“曲”的独立性。
北方剧种的“唱”堪称一绝,均兼有极强的叙事能力和抒情能力,可宏阔高远直上云天,亦可浑厚低回藏于谷底。京剧、豫剧、秦腔、评剧等剧种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都可称得上是中国一流的歌唱家,他们的“唱” 无需任何的配器便可占据整个舞台,他们的演员无需强化便已然是戏剧的中心。北方剧种的“唱”也由此更加的出彩,甚至成了“戏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