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
对于新媒体艺术展,观众作为群体来讲是开放的,但他们感受到的首先还是好玩和互动,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一定在乎作品中是否有更深刻的东西存在。

刘毅带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30名学生完成的特别项目作品《通》,在视觉上具有这种好玩的强烈吸引力,是现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刘毅设置主题后,让30个学生在黑板上各自写下自己想到的物件,再从这个物件出发去做一套可以穿戴的装置,要求是前一个人必须能用某种方式和后一个人连接在一起。去年看到这个作品,我立刻觉得,媒体艺术还是可以做到有诗意的表达。创作者使用的都是日常媒介,如:电话线,接电话,线团,风筝,拉链,浇花,吸管,雨伞,水泵……观者从中感受到一种机械时代的浪漫。”颜晓东介绍。

张辽源的有声灯光装置(LED落地灯、计算机、单片机、音响)在展览空间只有一盏落地灯位于中央,时明时暗不停变化着,观众可以辨别出背景声来自于一部电影,但影片的画面在现场是缺失的,视觉上唯一可感受到的光影变幻来自那盏灯——落地灯的光源由红、绿、蓝三盏LED灯组成,其亮度变化恰恰对应于影片原始数字文件中某个具体像素点RGB参数的实时变动。这件作品的接受度取决于观众对技术的理解力。对信息读取机制有了解的观众,才会对作品不符合常规的解构和再构成发生兴趣,如说明中提示:“作品从数字影像的媒介构成单元中抽取局部信息,简单地转换形式以后将这一局部信息的表达做了放大,并且与本身完整的声音信息再度构成一个新的呈现状态,一种多媒介信息内部的不对称性……但的确产生了新的感官、认知经验以及作品可能的表达维度。”

法国艺术家皮耶-劳伦·加斯耶(Pierre-LaurentCassière)的装置《风声》,是全场在形式上最单纯的一件作品:由一根穿过狭长空间的25米长的钢丝构成。观众可以通过触摸感受在钢丝内穿行的振动波,也可以将耳朵贴在钢丝上,听到振动波的声音。艺术家在山谷里录下不断变化的风声,合成样本并实时编辑成听觉信号,钢丝长度可以根据展览空间而变化。
互动声音装置《植物话语》是法国一对年轻组合“旋诺高斯汶”——格雷戈里·勒塞尔和安娜伊斯·梅德安丝(Scenoscosme-GregoryLasserre&AnaisMetDenAncxt)的作品。初看它只是悬挂在展厅过道处的几盆植物,特别之处在于其中的植物都有“唱歌”的能力,当观众接近或触摸,每一株植物都会给出感应,发出不同的声音。艺术家安娜伊斯告诉我,人体所携带的不可见的弱电是实现这种交互的关键,“如果阳光充足,植物也能随光源变化而歌唱”。从开始媒体艺术创作以来,她和搭档格雷戈里就一直在映射人和环境的关系,不过观众从他们作品中感受到的首先是一种温柔的、细微的叙述方式。

台湾“80后”艺术家姚仲函的声光作品《我会坏掉》通过控制电流,让一串荧光灯管以每秒16.6次开关的速度持续闪烁直至坏掉,但不知会在何时。“标题下的短诗和作品一样,精致、简单,有一种单纯的技术的美感:‘我会坏掉/坏掉前我的声音很美妙/我正以每秒16.6次开关的频率歌唱/我也以每秒16.6次开关的频率坏掉/然后完全坏掉/可以被丢掉。’”
生态

菲利斯·德丝蒂尼·德奥文(Felicied'Estienned'Orves)《锣》(录像装置,铝质装置,29'50",循环,直径2.4米。音乐:弗雷德里克·诺格瑞〔FrédéricNogray〕),2009年。
参展艺术家徐文恺是“80后”,他的身份相当有趣,代表了媒体艺术领域里新一代人的跨界特质:除了做艺术家,兼具计算机视觉程序设计师,这是大学里他攻读的专业。有一个Audiovisual工作室,可以在大型建筑环境上或LED覆盖物上做基于计算机的图形、图像。还和两个合伙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Co-workingEspace,将一栋老式四层洋房分割成不同大小的空间,按小时出租办公,最少可以租用一张桌子。“中国对媒体艺术感兴趣的人,大都知道一个网站:‘Weneedmoneynotart’(我们要钱不要艺术),最初这也是徐文恺和几个同学建起来的,开始是简单的互译,把澳大利亚一个博客网站‘Wemakemoneynotart’上面介绍新媒体的文章译过来,后来他们也把中国的新媒体艺术事件记录下来,译成英文回放到对方网站上去。对于介绍新媒体艺术来说,他这个网站是非常重要的。”颜晓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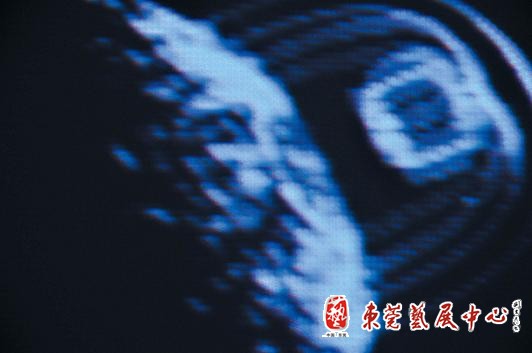

“我觉得在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点:美术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和收藏家,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可以支撑一些东西。相比之下,目前新媒体艺术的价值还无法得到转换,比如作品难以被收藏。如果一件作品用的是1999年的某代计算机,坏了要修或替换都困难,怎么收藏?这是现实问题。所有艺术都不是单纯存在的,有精神性层面,也有非常现实的层面,如果在现实层面受到约束,就很难蓬勃发展。与当代艺术相比,新媒体需要更新系统,这个系统不一定来自现有的艺术体系,也可能从其他领域借鉴。”目前在中国,除了最早涉及数字媒体和录像装置的胡介鸣等少数艺术家的作品有美术馆和机构收藏记录,新媒体艺术家很难依靠出售作品来生存,也比较个体化。
据颜晓东说,他熟悉的一位参展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到目前没有出售过,虽然有一份教职作为收入来源,做作品有时也要借钱。“年轻艺术家的生存方式大致就是两种:一个途径是为上海世博会这类大型展会设计制作新媒体表演,另外就是几个朋友合作,组建有一定综合能力的工作室。
一般来说,一件媒体作品的制作费很少低于1万元,因为需要购买媒材并反复试验。从展览中获得的报酬不足以支撑创作,比如我们这次展览给付的制作费在4000元到2万元不等,另外还有‘艺术家费’约7500元,这是支付艺术家到现场布展的费用,因为是上海和深圳两地展览,工作量比较大,费用比其他展览还要高些。但欧洲的标准比我们高得多,如果艺术家到场,这笔艺术家费用会在2000欧元以上。”关于系统和生态,法国已经有一种很好的转换方式。“法国媒体艺术活动始终与戏剧、表演、音乐、文学等传统文艺领域间保持着有效的互馈机制。在其他欧洲国家,也经常有这样的合作方式,比如几个剧场联合起来,把一个戏剧作品带到国内做巡回演出,费用分担。他们的新媒体艺术也借助了这种形式。”颜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