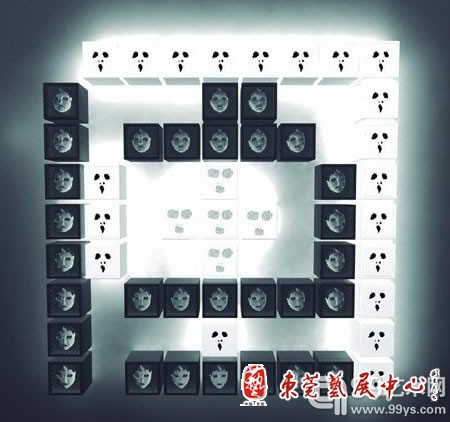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或许仅仅意味着杀毒软件的更新换代、手机应用的功能拓展或是邮箱的容量升级。然而,就文化遗产的存续而言,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一个专家小组日前发出警告,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英国的当代艺术地标将在十年内消失殆尽。换言之,数字时代的人们将彻底沦为艺术史上“失落的一代”。
科技与艺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过去几代人通过博物馆和书籍来凸显自己的存在:他们是谁?做过什么?然而,数字化时代的科技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保护能力。”朴次茅斯大学创新技术学院的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博士指出,永不停息的技术变革已对当代艺术收藏家及美术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保存一个三维可视化模型远比维护并恢复古代油画与雕塑作品要困难得多。
数字格式的迅速更新,CD、DVD及数字录音的升级换代总是令人措手不及、疲于应对,许多通过计算机创建的艺术作品早已佚失或无法读取。而新近诞生的互动型数字艺术作品如三维可视化文件和视频游戏等是如此错综复杂,“数字保护主义者”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如流星般稍纵即逝。
刚刚获得特纳奖提名的视觉艺术家希拉里·劳埃德(Hilary Lloyd)最近在伦敦Raven Row画廊展出的创新作品便是数字保护主义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异乎寻常的电影与录像组合方式几乎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所有期待。例如,看似静止的某个图像其实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投影机和显示器亦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
听起来很玄?至少对数字保护者来说,怎样完整而忠实地保存作品的色彩与视觉效果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这亦是以安德森博士为首的科学家近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铭记当下,反对遗忘——否则的话,“就好比走进一家举世闻名的美术馆,却只看到四面空白的墙壁”,沉溺于技术狂欢中的我们已在不知不觉间沦为“失落的一代”。
值得庆幸的是,数字保护正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据报道,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将于今年6月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及剑桥大学举行;剑桥中心的新数字艺术画廊亦于近期揭幕;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则为历史悠久的拉斯金画廊安装了最先进的3D等离子屏拱顶,力图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艺术试验场。
数字艺术保护:皇帝不急太监急?
相比于忧心忡忡的数字保护主义者,艺术家本人倒是显得相当淡定。
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电影及媒体高级讲师、视频艺术家西蒙·佩恩(Simon Payne)博士认为,数字艺术之所以如此“短命”,其实是创作者求仁得仁的结果,这种昙花一现的美感亦是观众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佩恩博士用“感性”来形容自己的作品风格。他喜欢和观众玩视觉游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视幻艺术是其最为钟爱的艺术母题之一。“理想的情况是在大银幕上营造出离散的物理效果,所以,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有效地保存它。”颇为讽刺的是,比起那些先锋性的数字艺术作品,通过电影胶片或录像带创作或记录的传统型作品反倒更容易流传下来,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严格说起来,很多时候数字艺术家都是抱着“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心态进行创作的。不过,佩恩博士亦承认,从学术角度看,重现昔日的艺术创作,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纪念,依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